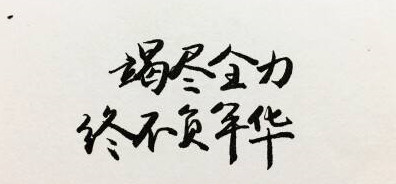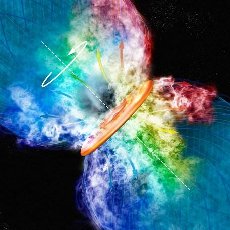摘要:
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有什么区别?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
摘要:
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有什么区别?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 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有什么区别?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
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内涵;而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学者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将具有“兴、观、群、怨”传统、主张用艺术来干预现实的儒家美学,看作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而将“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塞瞽旷之耳”的道家思想, 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取消主义的逆流。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大陆学者则又与港台学界彼此呼应,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中发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所梦寐以求的写意的风格和自由的境界,认为这才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却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了……。应该承认,以上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则又相互龃龉、彼此冲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这二者之间彼此“互补”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在我看来,尽管儒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式来加以分析,但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
一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则是以符号为载体和传媒的。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而以“相礼”为职业的儒者,最初恰恰是这种文化符号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下卷,第73页。)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孔子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便是最好的说明。当然了,孔子所开辟的儒学事业,绝不仅限于这种外在符号的掌管与操作,他要使职业的“儒”成为思想的“家”,就必须通过以“仁”释“礼”的方式,而为外在的行为规范(符号形式)找到内在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支持,从而克服文化符号混乱无序的历史局面,以保持世人的文化品味。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表明,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礼乐的复兴在孔子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标志着人与非人的界限。从政治的意义上讲,只有遵循礼乐本身所规范的行为法则和等级制度,才能使人与人在进退俯仰之间保持一种行而有等、爱而有差的和谐而有度的社会秩序,即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礼乐本身所具备的有意味的符号形式,才能使人与人在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交往中保持一种高于蒙昧和野蛮色彩的文明形象,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尽管在孔子那里,文化的建构是要以生命的繁衍和物质的保障为前提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然而这种“庶”——“富”——“教”的渐进过程也表明,文化的建构才是使人最终成其为人的关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一向强调忠孝安邦、礼义治国的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之类的喟叹。
显然,在这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种艺术的经验和美的享受。因为说到底,“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质上是一种符号”,这类包含着艺术和美的“符号体系”,“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中给予我们以秩序”,“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175、214、189页。)。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人在《乐记·乐本篇》中似乎已有所领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通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在这里,声、音、乐三者的区别,标志着禽兽与人、野蛮的人与文明的人之重要区别。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是说由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当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没有进入符号系统,还只是一种无法通约的声响时,它便等同于野兽的嚎叫:虽然也表达了一定的情绪,却无法加以辨别,也没人可以听懂。只有当这种声响进入了符号的系统,它才是一种主观情感的“人的”表达方式,即“声成文,谓之音”。这里的“声成文”,既可以理解为声响通过交织、组合而具有文彩,又可以理解为声响进入表义的符号网络而具有文意。事实上,只有当自然的声响进入了表义的符号系统,才可能具有无限丰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动物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但是由于这些声响既无法在符号的意义上加以
区分,更无法在区分的基础上加以组织并重构,因而总归是单调的。说到底,而无论文彩还是文意都只是人才具有的,这正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所在,“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进一步讲,声音一旦进入了符号系统,便不仅具有了通约的可能,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即“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因此,如果人们只知道声音可以传达情感而看不到这种情感背后所潜伏的只有人才具备的伦理内涵的话,那么他充其量也还只是个野蛮的人而不是文明的人,故曰“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所谓“惟君子为能知乐”一句,抛开儒家的阶级偏见来看,它指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人对于美的多样形式和多层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孔子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所奠定的这一套“郁郁乎文哉”的伦理规范和典章制度,古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不仅会变得杂乱无章,而且会显得单调无趣。甚至还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儒家为建构礼乐文化所进行的历史性努力,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将会在很长时间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之中。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宋人的那句多少有些夸张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从“符号系统”的角度来讲,孔子所重建的这套礼乐文化囊括了诗、乐、舞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关于“礼”和“乐”之间的关系,《乐记·乐论篇》中有一段言简意赅的分析:“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就是说,“乐”可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礼”可以辨别长幼尊卑之界限。光有“乐”而没有“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会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级观念;光有“礼”而没有“乐”,不同地位的人就会离心离德,缺乏沟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乐”助“礼”,以“礼”节“乐”,从而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爱有差等的境界。由此可见,“礼”、“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仁”、“礼”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而作为这一表现的情感符号,广义的“乐”又是由语言(诗歌)、旋律(音乐)、动作(舞蹈)三个要素组成的。合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共同伴随着礼仪而沟通着人们心灵的时候,它便会引起一种情感的共鸣和美的享受。所以《论语·学而》才会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论述。分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得到独立发展的时候,它们便会成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并各自发挥其美的功能。所以,对于诗,孔子才会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训导;对于乐和舞,孔子才会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之类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诗、乐、舞等表现艺术相对发达的历史特征便可以在儒家以礼乐来建构文化的独特方式中找到根据。
儒家建构礼乐文化的这种历史性努力,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习惯的形成和艺术价值观念的确立是影响巨大的、深远的,甚至夸张地说,是从无到有的。但是,这种由伦理的观念符号而衍生出来的艺术的情感符号又有其先天的弱点和局限。在形式上,由于后儒并未真正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的深刻含义,因而不断地在“礼”的外在形式上大作文章,从而在《周礼》、《仪礼》、《礼记》等著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套举世罕见的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冠、婚、丧、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都必须经受严格训练,受其影响,“乐”的形式也由简到繁,成堆砌雕琢之势。在内容上,由于“礼”的等级观念始终规范着“乐”的自由想象,致使艺术的形式发展得不到观念更新的配合与支持,以至于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模式中转圈子,由中庸而平庸。于是,最初是富有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便导致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道家的“解构”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二
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另一个逻辑环节——“无”。如果我们用这对范畴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儒家的建构目标便是“有”,道家的解构目的则是“无”。同黑格尔观点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解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
作为这种历史性的回归,道家的创始人首先在伦理政治的层面上对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提出了质疑。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庄子更为激烈,他直接对“圣人”讨伐道:“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儒家伦理,是因为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曲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确实具有着反抗异化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老、庄所反抗的异化现实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在哲学的意义上加以肯定。在反抗儒家伦理的同时,道家的创始人还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所建构的那套文化符号体系,并企图加以彻底地解构和颠覆。老子主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庄子更为激烈,干脆断言:“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 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 胠箧》)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又确实具有某种反文化的色彩。但是,由于道家这种反文化的倾向是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前提的,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又不能简单地在美学的意义上加以否定。换言之,道家的“无”是针对儒家的“有”而言的,道家的“解构”是针对儒家的“建构”而言的,因此,无论是在哲学的意义还是在美学的意义上,对道家的理解都必须是以对儒家的评判为前提的。
在美学的意义上,道家对儒家所建构的礼乐文化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解构文饰,即消除文明所附丽在物质对象之上的一切修饰成分,使其还原为素朴的混沌形态。我们知道,孔子在强调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前提下,对“文”还是相当重视的,所谓“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就是对尧之时代所创立的雕琢文饰的感官文化的赞誉,所谓“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就是对禹之时代所创立的绚丽多彩的礼仪服饰的褒扬,而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则正是“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必要前提。在谈到人之修养的时候,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文之以礼乐”,即是把礼乐作为一种文饰而附丽在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高贵的品质和文化的意味。在谈到文章辞令的时候,孔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修饰之”、“润色之”,显然是一种辞章的加工和语言的装饰。在谈到艺术欣赏的时候,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这里所谓的“洋洋乎盈耳哉”,则无疑凝聚了艺术家的手法和匠心。这种思想,在后儒那里表述得更加明确,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然而这一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见《论语·学而》引《诗经》句)的文化努力,在道家看来则恰恰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老子认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也!如此说来,一切人为的努力、文明的追求,非但不能接近“道”的原初境界,反而背“道”而驰,创造出一大堆虚假、扭曲、芜杂的文化垃圾。——“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这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的情况下,他主张,不如放弃过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在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中体验纯洁而原始的生命乐趣,进入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境界。庄子及其后学也对那种雕琢和文饰的人为努力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庄子·秋水》)因而主张“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老、庄解构文饰的这一努力,并非只具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寻求着一种回归自然、法天贵真的新的美学意义。
其次,道家在解构物质对象之外部文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解构儒家创造文化符号所遵循的内在法则。我们说过,在孔子那里,“礼”和“乐”这类文化符号是“仁”和“礼”之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因此,作为特殊的“情感符号”,艺术所遵循的创作法则完全是以其“过犹不及”的行为标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来决定的。孔子一向是主张以理节情、“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的,用颜渊的话来说,就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以这样的法则来对待艺术,才能够创造出《关雎》之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佳作,并起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之类的警示作用……。然而在道家看来,既然儒家所遵循的那套伦理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用这套标准来规定艺术的功利价值,则更是不得要领了。老子认为,不应该以艺术为手段来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应让人的生活和艺术遵循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以进入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为前提,人们的艺术活动才能够实现自由的想象和不断的创造,即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似乎比儒家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更加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庄子及其后学也认为:“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乘物以游心”的人生——艺术境界。所谓“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才能够“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就象庖丁解牛一样,只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够“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乃至于“砉然向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由此可见,老、庄对艺术法则的解构,只是要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并不是要践踏客观的自然规律;相反的,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上,道家的“解构”活动则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意的。
在解构文饰、解构法则的基础上,道家思想的极端性发展便是对于文化现象之载体的语言符号体系的解构。我们知道,早在孔子之前,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符号体系就已存在,只是由于缺少伦理价值观念的支撑,使得这一体系十分松散、很不牢固。而儒家的所谓“建构”,就是要以“仁学”的价值观念来支撑“礼乐”的符号体系,以克服“礼崩乐坏”的局面。针对当时文化符号体系混乱的现状,孔子曾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慨叹。在他看来,“觚不觚”这类表层符号的混乱,意味着“君不君”、“臣不臣”等等深层价值观念的动摇。因此,他竭力主张以“正名”的方式来重新整顿价值观念和符号体系,并理顺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事实上,在孔子表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语言符号的运用是十分讲究并充满信心的。例如,在谈到仁人的品格时,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谈到诗歌的艺术功能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尽管儒家对逻辑学和修辞学并不太感兴趣,但所有这一切,至少能说明孔子等人对语言符号的肯定态度……。然而在以“解构”为能事的道家那里,对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则刚好相反。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在他看来,真正本体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语言符号来加以表述的,一旦我们用有限的符号来形容“道”的时候,这个本体的无限意蕴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在他的影响下,庄子也看到了语言符号的局限性:“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并进而指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如此说来,由形色名声所组成的整个语言符号系统,都已在解构之列了。然而庄子解构语言符号系统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这一系统,而只是为了借助语言来达到超越符号的意义。《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由于这种表面符号的解构同深层意蕴的追求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同解构文饰、解构法则一样,老、庄解构符号的努力也并非是全然消极的,事实上,它恰恰在另一个层面上接近了艺术语言的奥秘。
从以上的三重解构中可以看出,道家对中国美学的历史贡献,恰恰是作为儒家美学的对立面而得以呈现的。从审美理想上看,素朴本身并不美,只有反朴归真才是美。因此,如果没有儒家所建构的远离原始形态的礼乐文化,那么道家所追求的那种“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生活状态便毫无审美价值可言了。从艺术门类上讲,如果说儒家美学与乐舞之间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那么道家美学则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盛唐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主张:“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诀》)这其中显然包含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晚唐画论家张彦远认为:“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彩;云雪飘飘,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这其间无疑渗透着庄子“得意而忘言”的精神。因此,大体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示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由庄子所显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只是我不太同意将儒、 道的这两种艺术精神用“纯”与“不纯”来加以区分。如果说儒家美学是强调“善”的,其极端性发展必然导致“伦理主义”;那么道家美学是追求“真”的,其极端性发展则难免导致“自然主义”。就其终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们谁也不是纯“美”和纯“艺术”的。然而,“美”和“艺术”却恰恰处在“善”与“真”、“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因此,正如儒家的“建构”需要道家的“解构”来加以不断地清洗以避免“异化”一样,道家的“解构”也需要儒家的“建构”来加以不断地补救以防止“虚无化”。事实上,正是在儒、道之间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的推动下,中国美学才可能显示出多彩的风格并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
总之,与儒家以“建构”的方式来装点逻辑化、秩序化、符号化的美学世界不同,道家则是以“解构”的方式寻求着一个非逻辑、非秩序、非符号的审美天地。如果说,儒家的努力是一种从无到有、由简而繁的过程,其追求的是“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不纯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的境界;那么道家的努力则是一种删繁就简、去蔽澄明的过程,其追求的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境界。
请采纳,谢谢
有关道家学说的论文~~哪方面都行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仙”与“道”的结缘,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时代,神仙思想已经孕育成型。庄子在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时,继承了老子首创的道家学说,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庄子正是因为最早将“仙”与“道”结合在一起,使道家学说和神仙思想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庄子》“外篇”和“杂篇”是否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历来争议较大。鉴于此,本文探讨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就以《庄子》“内篇”为主要考察对象,“外篇”与“杂篇”的相关内容仅用于参照和补充。
一
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定《庄子》一书中涉及神仙思想的那些篇章,或是庄子后学的作品,或是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渗入的部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多认为庄子本人还不可能具有神仙思想。其实,庄子时代神仙思想早已形成,庄子本人也具备接触神仙传说的客观条件。
这里所谓“神仙”,指的不是“神”和“仙”,而是专指“仙”。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神”与“仙”原本并不属于同一类别。古人在造字时,“神”字是“从示”,而“仙”字则是“从人”,二者之间的区别相当明显。《说文解字》云:“仙,长生仙去。”刘熙《释名·释长幼》亦云:“老而不死曰仙。”看来,在汉代人的眼中,“仙”就是长生不死的人。又《汉书·艺文志》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可见,“神仙”指的同样也是长生不死的人,“神仙”其实也就是“仙”。那么,“仙”为何又称“神仙”呢?闻一多先生解释说:“人能升天,则与神一样,长生,万能,享尽一切快乐,所以仙又曰‘神仙’。”的确如此,“仙”不仅能够长生不死,而且还兼具不惧水火、往来云中等神性,因此“仙”又称“神仙”。
那么,神仙思想最早产生于何时呢?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末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些有关长生不死的传说,神仙思想已经初显端倪。《左传·昭公二十年》云:“齐侯(齐景公)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又《韩诗外传》云:“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蓁蓁。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以上这两则材料都记载了齐景公对于“古而无死”的羡慕和向往,由此可知,早在齐景公所处的春秋晚期,长生不死传说就已经产生。追求长生不死乃是神仙思想的核心内容,长生不死传说的出现标志着神仙思想已经萌芽产生。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齐、燕沿海地区已经掀起了一个人海求仙的热潮,《史记·封禅书》对此已有明确的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庄子之时,楚地的神仙思想也颇为盛行。《山海经》、《楚辞》等文献典籍中就保存有楚地流传的一些“长生不死”传说。据袁珂先生考证,《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的楚国或楚地人所作海外南经》中有“不死民”:“其为人黑色,寿,不死。”《海外西经》中亦有“轩辕国”:“其不寿者八百岁。”屈原《天问》云:“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又云:“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屈原所问的,就是楚地流传的“长生不死”传说。《山海经》中还出现了“不死药”,如《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大荒西经》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天问》也问到了“不死药”:“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问》还问到了蓬莱仙话中的“巨鳌负山”传说:“鳌戴山扦,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楚地还发生过向楚王献“不死药”的事,《战国策·楚策》曰:“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可见,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已经在楚地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战国时期,百家竟起,自由争鸣;舌辩之士,朝秦暮楚,四方游说;诸侯国之间亦遣使往来,交流频繁。宋国地接齐、楚,作为宋之蒙人,庄子自然能够接触到齐、楚两地广为流传的神仙思想;而《庄子》(主要是指“内七篇”)中的“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能够彻底超越时空限制、获得生命永恒与自由的“得道者”形象,正是受到了神仙传说的影响。
庄子是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庄子在继承老子道家学说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并且创造性地将它们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庄子哲学中,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道”,第一次实现了它与“仙”的结缘。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合于“道”则生,不合则亡。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又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侯王无以正,将恐蹶。”对此,庄子既有明显的继承,又有长足的发展。《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猗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项得之,以处玄 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认为“道”尽管“无为无形”、“不可见”、“不可受”,但它却是“可得”的。庄子将黄帝、颛顼、禺强、西王母等能够获得某种超自然神性的原因,全都归结为“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黄帝、西王母、彭祖、傅说等都是神仙传说中有名的神仙,而彭祖和傅说又是早期仙话传说中典型的“仙人”。任何生命体的存在,皆有一个无法超越的时间极限,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神仙家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世人通过服药、修炼等途径,是可以成仙的;而人一旦成了仙,就打破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极限,生存时间无限延长,甚至长生不死。仙话传说里的人物,常常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前后相距竟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彭祖就是早期仙话传说中著名的长寿仙人。
庄子认为,彭祖、傅说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仙,就是因为他们得了“道”。庄子创造性地把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结合了起来,借助超现实的神仙思想更进一步地去充实、美化、鼓吹和宣扬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使“道”具有了更大的诱惑性和吸引力。
庄子出于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目的,吸收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神仙传说,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提炼和升华,创造出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的“得道者”形象。庄子笔下的这些“神人”、“至人”、“真人”等,名异而实同,他们都是“道”的化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平四海之外。(《齐物论》)
(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人火不热。……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大宗师》)
这些“神人”、“至人”、“真人”身上,都有着浓厚的神仙气息。他们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形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神人”、“至人”、“真人”所具有的超自然神性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物不能伤其身。《齐物论》中的“至人”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是“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二是可以乘龙、驾云,自由往来于空中。《逍遥游》中的“神人”可以“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的“至人”也可以“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三是独特的饮食生活方式。《逍遥游》中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大宗师》中的“真人”也显得与众不同:“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笔下的这一系列“神人”、“至人”、“真人”等,都是作为“得道者”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在庄子哲学中都是“道”的象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三个方面的超自然神性,也正是神仙传说中神仙超越凡人的地方。除了具备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之外,庄子笔下的“得道者”还兼具“长生不死”的特点,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彭祖和西王母。此外,还有《大宗师》中“年长”而“色若孺子”的女偊,《在宥》中“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常衰”的广成子等,也都是“长生不死”的奇异之人。“长生不死”正是神仙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神仙最令世人向往的地方。由此看来,庄子塑造“神人”、“至人”、“真人”这一系列“得道者”形象的原始素材,应该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
庄子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引入道家学说,塑造了“神人”、“至人”、“真人”等一系列“得道者”形象。这一系列来源于神仙传说、具有超自然神力、带有浓重神仙色彩的“得道者”形象,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加诱人的宗教般的新境界。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神仙思想尽管已经孕育成型,但毕竟还只是处于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神仙传说都还是比较零散的,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神仙学说,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神仙修炼方术。而当时在齐、燕沿海地区新兴的所谓“方仙道”,其所鼓吹的神仙修炼方术也不过是“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早期的神仙方士们还不可能给梦想成仙的世人提供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神仙修炼方术。庄子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思想与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结合在一起,鼓吹和宣扬道家学说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条“修道成仙”的途径。
对此,庄子不仅在理论上为神仙方士们指明了一个“得道升仙”的美好前景,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套诸如“心斋”、“坐忘”、“悬解”等具体的“修道”方法: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仲尼)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大宗师》)
“心斋”就是要心志专一,排除各种杂念,始终保持虚空的心境。从用耳去听,到用心去体会,再到用气去感应,逐渐提高,直至达到与“道”相合的境界。“坐忘”就是要静坐、静修,忘却形体,闭塞视听。通过彻底忘记自己与周围世间万物的区别,从而实现整个身心与“道”的完全融通。“悬解”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解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烦扰,真正进入清静、虚空的修道境界。庄子不仅给神仙方士们提供了“心斋”、“坐忘”、“悬解”这些具 体的“修道”方法,而且对于“修道”的过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丽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庄子认为“修道”需要经过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放弃追逐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接着是抛开个人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享受,再就是完全忘却自己的肉体生命。完成这一阶段后,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清净、明朗,然后就能用心观“道”,渐渐地与“道”相合,渐渐地超越古今,最后完全进入“不死不生”的“得道”境界。庄子所描述的这些“修道”方法和过程,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实践性,为后世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修道成仙”的重要模式。
体的“修道”方法,而且对于“修道”的过程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吾犹告而守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丽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庄子认为“修道”需要经过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要放弃追逐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接着是抛开个人身体所需的各种物质享受,再就是完全忘却自己的肉体生命。完成这一阶段后,内心自然就会变得清净、明朗,然后就能用心观“道”,渐渐地与“道”相合,渐渐地超越古今,最后完全进入“不死不生”的“得道”境界。庄子所描述的这些“修道”方法和过程,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可实践性,为后世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修道成仙”的重要模式。
总的来说,庄子哲学中“仙”与“道”的结合,进一步美化了道家学派理想中的“道”的王国,将道家学派所崇尚的“道”提升到了一个更为神奇、美妙的宗教般的新境界;同时在客观上也为神仙方士们提供了一套“修道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使神仙思想彻底超越了原始的巫术、方术,沿着宗教神学的方向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后世神仙道教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正因为如此,庄子才成为后世道家和道教共同尊崇的重要人物
道家学说提倡什么 ?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等政治、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